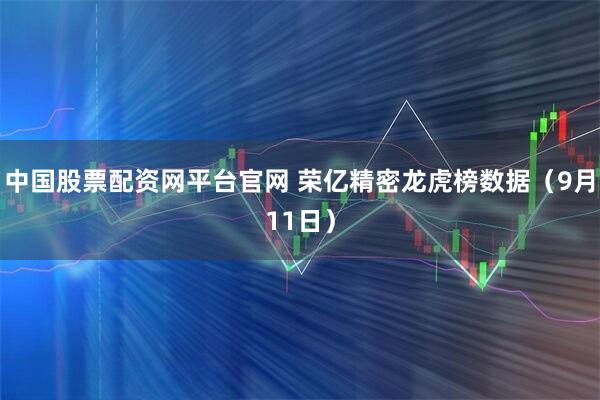“故乡的风挽着母亲河的水,心里的苦渗着油盐的味,滚烫的雨终将会汇,长天共秋水,咿呀咿子哟,看鸟儿往南飞……”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傍晚漫出窗台,像一缕扯不断的丝线,轻轻勾连着年少的记忆。那时我走在街头,望着四周拔地而起的楼房,总觉得故乡是方方正正的天井 —— 左邻右舍的红砖墙向上延伸,稳稳框住一方天空;院子口的老槐树枝繁叶茂,浓荫悄悄掩住半条街巷;就连课本里提及的母亲河,也只在泛黄的插画中泛着朦胧光影,遥远得像一场未醒的梦。
那时的脚步总被门槛轻轻绊住,以为世界的边界就在巷口:是清晨巷子里 “豆浆油条” 的叫卖声,热气裹着香气钻进鼻腔;是坐在父亲自行车后座,透过懵懂的双眼看见的街景 —— 路边的梧桐叶、来往的自行车、街角杂货店的霓虹灯,便构成了我认知里的全部天地。从未想过,青砖矮墙之外,竟有漫山遍野的风呼啸而过,能牵起一整条河的粼粼波光,把更辽阔的风景铺展在远方。
展开剩余87%年少的我总把 “闯荡” 挂在嘴边,仿佛这两个字能生出翅膀。课桌上用铅笔刻满歪歪扭扭的航线,每一道划痕都指向未知的远方;日记本里抄满陌生的地名,北京的胡同、上海的外滩、三亚的海浪,字字句句都藏着对世界的渴望。那时总愤恨自己空有双腿,却走不出故乡的方寸之地;骑单车掠过街角时,又嫌巷弄太窄,容不下一心向外的念头;嫌母亲河的水流太慢,赶不上追逐远方的脚步;更嫌夕阳落得太急,还没等我看清对岸芦苇的模样,就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,像一声无奈的叹息。
直到十年后,我骑着一辆旧单车再度出发。一段逆风爬坡的路,汗水浸湿了衣衫,双腿也渐渐发酸,可当我抵达高处回头望时,却忽然愣在原地 —— 原来故乡才是汇聚天下山水的原点,那些曾经向往的远方,不过是从这里延伸出的脉络。风依旧是故乡的风,水依旧是母亲河的水,只是这一次,我终于读懂了它们藏在时光里的温柔。
体检报告上 “脂肪肝” 三个字,如一记闷棍,重重敲在我的太阳穴上。那辆陪伴我六年求学,而后又被搁置两年的老单车,被我从楼道角落里拖了出来,灰尘簌簌落下,仿若一场迟来的雪。推出它的那天,光柱里的灰尘翩翩起舞,当指尖触及左车闸上粗糙的纹路时,那些 “紧刹慢赶” 的岁月瞬间如潮水般涌来。初中时,我骑行在两公里的街巷,父亲总是在身后大声呼喊 “靠边走”。可曾有一次,一辆红色轿车的车门如翅膀般突然展开,我连人带车飞了出去,左膝的鲜血染红了半条裤腿。父亲冲过来时的神情,比我受伤还要痛苦,他紧紧攥着我的胳膊,手背上青筋暴起,那一刻,我首次明白,有些疼痛会穿透皮肉,径直扎进亲人的心底。换链条、补车胎、调试变速,师傅的扳手叮叮当当响着,当我第一次蹬车踏上八一广场,膝盖里那枚 “旧钉子” 又开始隐隐作痛 —— 幼年骑行途中,种种突发状况留下的伤痛如同定时器,时刻提醒着我曾因胆怯而 “紧刹慢赶且徐行”,可如今,我必须要用同一条腿,把逝去的健康重新夺回。于是清晨七点,父亲会为我扣好头盔;傍晚七点,爷爷会扶着门框呼喊 “早点回”,只是那声音被病痛扯得有些破碎。我把他们的叮嘱小心折叠,放进骑行服的口袋,蹬起第一圈踏板时,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骑出去,把健康骑回来,把时光骑得慢一些。
出城向北 12 公里,浊漳河将城市轻轻揽入臂弯,再往前便是漳泽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—— 这片 58.72 平方公里的 “城市之肾”,24 平方公里的浩渺水面,宛如被太行山高高托起的月亮。
破晓之际,我沿着滨湖大道疾驰,左手边是波光粼粼的水面,右手边是渐渐苏醒的芦苇荡,神农大桥的斜拉索在雾气之中伸出七根银弦,微风拂过,便弹奏出低沉的 C 大调。桥下,苍鹭贴着水面如白色闪电般划过;桥上,我的车轮与心跳同频共振,身体仿佛先于灵魂抵达了 “自由” 二字的真谛。穿过气象塔北面的柳林湿地,杞柳排列得整整齐齐,枝条垂落似绿色雨丝,古人常借柳抒别离之情,我却在柳荫之下学会了与自我和解。木栈道蜿蜒曲折,浊漳南源的引水溪流在脚下叮咚作响,野花肆意绽放,仿佛是在替我将童年的跌跌撞撞一一缝补。
再往南是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的十里风荷,六月的风吹开那无边无际的碧叶,荷花高高挺立,超过人头,犹如一盏盏粉色的明灯。我推车缓缓前行,看着白鹭静立在卷起的荷叶边缘,恰似一枚别在绿绸之上的银别针,恍惚间,想起课本里杨万里笔下的 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也忆起祖母曾用荷叶包裹蒸馍,那清香渗入麦香之中,成了她留给我最柔软的味觉记忆。
芦荻湾东侧,二十四座桥将 73 座小岛串联成一首长长的诗篇,汉白玉的安澜桥、木拱的梦湖桥、石拱的倚秀桥…… 每一座桥栏之上,都雕刻着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的浮雕,月光洒落,神话故事仿佛瞬间活了过来。我推着车从荷风桥走到玉心桥,每一步,都踩碎了一片自己的倒影。傍晚返程,
我把单车停靠在城市阳台的栏杆之外,夕阳如一枚熔金的印章,啪嗒一声盖在湖面之上,鳞状的波纹仿佛成了一封写给天空的长信,太行山的脊线被晚霞剪出如剪纸般温柔的轮廓,湖心岛上成群的白鹭同时振翅高飞,好似有人扬起了一把洁白的雪。此时,手机弹出父亲的消息:“你爷今天吃了一碗面,精神好。” 我回复给他一张湖面的照片,并附上留言:长天共秋水,我们都被这片水稳稳托住。
骑行经过八一广场的喷泉时,水珠飞溅到脚踝,凉意如同高三那年的雪。又想起初中时,总是跟在哥们身后疯狂骑行,他为了追逐一个姑娘,能把单车蹬到八十迈,我则紧紧攥着车闸在后面大喊,生怕他撞上路边的法国梧桐。那姑娘的马尾辫在风中飘扬,像极了漳泽湖春天里摇曳的芦苇,可后来,我们都断了那份念想,唯有那次狂飙时的风声,依旧藏在车铃之中。
路过长治一中的红砖墙,红灯倒计时在眼前闪烁,忆起高一那年,第一次听到 “梓蕤” 这个名字,女老师站在讲台上,阳光把她的影子投射到黑板报上,粉笔字簌簌落下。后来分去文科班,两位男老师总爱说 “人要站得直”,他们的声音比操场的哨子还要响亮,吹散了那时萦绕在我心头的迷雾。骑行到 “三河一渠” 的岸边,秋阳把河水晒得金光灿灿,这两年河道变得清澈,两岸的树木也愈发葱绿,可祖母却没能等到亲眼目睹的这一天。曾经与父亲漫步在河岸,幻想她在身旁,背着手缓缓前行的模样,不禁潸然泪下,而这时,一阵风拂过我的脸庞,我知道,她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。
不得不承认,眼前这般美好的景致是近几年才有的改变。浊漳河曾经漂浮着塑料袋与煤灰,漳泽湖也因采砂变得千疮百孔,祖母在世时,总是感慨 “水又黑又臭,鱼也活不下来”。她好不容易等到了水变清的那个夏天,可惜却没能和我一同走进这条静谧、安详且清新的河道。自 2016 年起,长治启动了 “三河一渠” 综合治理工程:关停排污口、退渔还湿、栽植了 160 万株芦苇与香蒲,搬迁了 8 个村庄、让 130 多家企业退出。如今的湿地公园里,青头潜鸭、大天鹅、白琵鹭等鸟类陆续回归 —— 它们如同远方的亲戚,带来了湿地复苏的喜讯。
我骑行穿梭其间,仿佛置身于一幅徐徐展开的青绿山水长卷:春天,看浅草没过车轮;夏天,看荷叶为白鹭撑起绿伞;秋天,看荻花替秋风梳理发丝;冬天,看大雪为湖面重新梳妆。然而时光终究无情,祖母骤然离世那年,我第一次在河渠边哭到喉咙沙哑;今年,爷爷的膝盖已支撑不起拐杖,父亲鬓角的白发也像盐粒一样撒进了黑夜。我把他们年轻时的合照塞进骑行背包 —— 照片中的他们,站在尚未修缮的漳泽湖荒滩之上,背后是灰蒙蒙的天空。如今,我替他们来见证这碧水蓝天,替他们多呼吸一口带着芦苇甜香的空气。
夜色降临,我打开车灯,一束锥形的光照破黑暗。湖心岛的灯光依次亮起,如同有人在水面撒下了一把星星,我放慢车速,也让心跳逐渐平缓 —— 骑行的意义在这一刻变得无比辽阔:它不只是我摆脱脂肪肝的自救之举,更是我以滚动的车轮为故乡谱写的诗篇。回到家中,我把一天拍摄的影像裁剪成九宫格:第一张,是神农大桥的拉索挑破晨雾;第二张,是白鹭掠过十里风荷;第三张,是二十四桥的月亮倒映在桥孔里…… 最后一张,是城市阳台上那枚熔金般的落日。我把这些照片发送给曾在故乡一同成长的小伙伴们,微信消息瞬间炸了锅 ——“这还是咱长治?”“芦苇比人高,荷花比脸大!”“等我,国庆就买票回家!” 我又把原图传给云州平城的朋友们,他们纷纷回了一连串的 “震惊” 表情,并说道:“人说山西好风光,人说上党好风光!” 我把手机放在窗台,夜风从漳泽湖吹来,带着潮湿的芦苇香气,穿过我的指缝,也穿过了父亲刚刚发来的语音:“慢慢骑,不着急回家。”
那一刻,我分明懂得 —— 祖母苦等未见的澄澈碧水,爷爷再难踏上的蜿蜒长堤,父亲总来不及细赏的绚烂晚霞,此刻都悄悄融进我车轮碾过的辙印里,随着每一次蹬踏,缓缓延伸向更远的时光。骑行里程表的数字跳得愈发轻快,我的双腿却似卸下千斤重担,愈发轻盈。从前总怨脚下路途有限,走不进远方的风景,如今才恍然醒悟:故乡早把世间山水的灵秀,都揉进了吹拂耳畔的风里,漾在眼底流淌的水中。左膝的疤痕依旧清晰,却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勋章 —— 它刻着年少时的莽撞与跌撞,也藏着故乡从未缺席的温柔与包容。
风又起了,携着漳泽湖的粼粼波光,轻轻淌进心底。远处的神农大桥亮起暖黄的灯,城市阳台的剪影浸在暮色里,朦胧得像祖母年轻时哼过的老歌谣,温柔又绵长。原来所谓故乡,从不是地图上一个固定的坐标,而是无论你闯荡多远,总有一缕风会循着来路牵你回家,总有一河水会守着时光等你归来的地方。
“故乡的风牵着母亲河的水,心里的甜酿的是岁月的味,归来的人终会依偎,乡愁融秋水,咿呀咿子哟看炊烟向山飞”,收音机里的旋律换了新词,却依旧绕着故乡的情愫。我踩着单车往家的方向慢骑,车轮碾过路边落叶,发出细碎的 “沙沙” 声,像是在与耳畔的风、远方的水,轻轻应和着这趟关于归途与眷恋的旅程。
发布于:河南省富华优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